十一、什麼也沒說
十二、香嚴上樹
十三、穿山越嶺的禪曲
十四、如藤倚樹
十五、見性是什麼
十六、殊勝的金剛經
十七、傳心即傳燈
十八、彩虹的故鄉
十九、獨釣金鱗
總共 37 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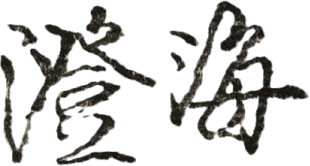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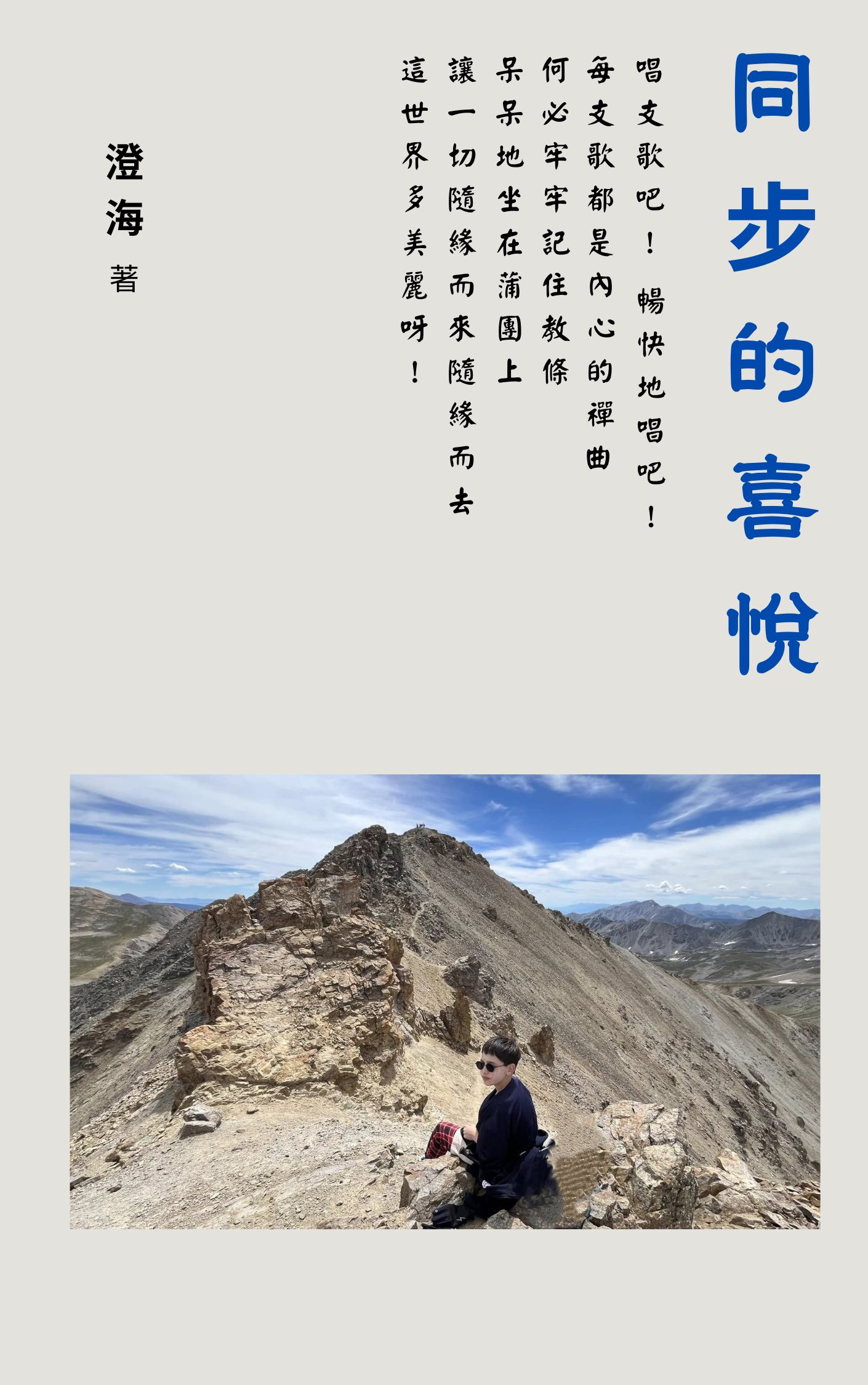
禪是活潑生動的生命源頭,自然蘊含著讓人感到溫暖的光熱,因此,一個開悟的人充滿了熱情,洋溢著神采,散發著幽默的語言動作。
我們很難想像,一個鐵板似的臉,劃著嚴肅的相貌,一天到晚講道理的人,他是開悟的人或禪師。縱然,他必須講道理,也會讓氣氛融和,使會場充滿青春的氣息吧!不然怎麼會是開悟的智者呢?
像雲門文偃禪師(864-949),生就一副帝王相,圓悟禪師稱「韶陽出一句,如利刀剪卻」,氣勢逼人,卻也真的老婆心切。
可是,他也是個非常幽默的人。
有人問:「何謂祖師西來意?」
他毫不猶豫地說:「是什麼乾屎橛」、「還我話頭來」。
有人說「佛陀出生,一手指天,一手指地,周行七步,說:天上天下,唯我獨尊。」
他卻說:「當時若在,殺了餵狗,免得禍亂人間。」
不用討論這種言詞舉動的涵義,光模擬他們師徒擠在禪堂,言詞交鋒,出言吐句,顧盼的神態,實在令人心儀不已。
那是一個歡樂、自由、奔放、毫無顧忌的地方,充滿真情的交流,多麼令人心嚮往之啊!
記得民國五十年,胡適先生回國,在台大法學院演講,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,他竟真的跳起身來,結果摔了一跤。那種率真無偽,融於真理的忘我神態,一直栩栩如生地留在腦際,他真是有血有肉的人呀!
沒有真感情,怎麼會有血有肉?沒有真感情,怎麼肯全副精神表達他的關懷?沒有真感情,怎麼會把他的生命貢獻於社會呢?
耕雲老師就是這樣富有真感情的禪行者。許多弟子到他家拜訪,等於作客,他老人家親自烹茶送煙。侷促斗室,他也沒有嚴厲的教訓,只在春風拂面中閒話家常,法本法無法,將他的般若無聲無息籠罩在弟子內心中,無法法亦法。
直到有一天,他為弟子講完〈心經釋疑〉,簡答了弟子提出的各種疑問,臨別之前,他只有點傷感地說:「幾年來講法報佛恩,大家都容光煥發了,生命盎然了。但本人卻日漸消瘦,惹了一身病痛,只好告別了。」
那一幕,讓我的頭低下又低下,低到地上,羞愧得無地自容。然而耕雲老師的感情是全部付出的,期待著法界的心燈永遠明亮。期待還在,心燈何處續燃?
沒有全生命、全感情的投入,學禪絕不會成功。相對地,一位真正的禪行者,他講法授徒,也是全生命、全感情的付出的。
從這種深切的體會中,才可以稍微了解禪的無私光明、正直偉大。
一千一百年前,百丈懷海禪師(720-814)站在禪堂上,望著眾多的弟子,清亮地唱偈:
「靈光獨耀,迥脫根塵。
體露真常,不拘文字。
心性無染,本自圓成。
但離妄緣,即如如佛。」
原來,偉大的禪師正將豐沛的生命能量,灌輸進弟子的心中,讓心心相映,般若智光相照,完成一場師徒同沐聖光。
那是無上灌頂,圓滿灌頂呀!
那是無形相的「洗禮」呀!
開示結束,大眾施禮而退。
百丈禪師目送弟子走向堂門,他又叫住他們問:「是什麼?」
千叮嚀,萬叮嚀,是否把剛才送給你們的般若好好地保持了呢?
然而,再也聽不到那句「是什麼」了!
千里同風,「平等法施,豈有厚薄?」音聲漸稀,法音流暢,容顏依舊深烙,畢竟娑婆世界飛逝了五年歲月。
想起您微笑的嘴角,
想念您偉壯的嚴肅,
晃盪著迷濛的煙霧,
而茶香飄著,流著,飛著……。
機緣是無可捉摸的靈感,來無影、去無蹤,而相會只是剎那。
洞山良价寫完〈過水偈〉,靜靜地想著慈師雲岩和尚的相貌,如果在臨別的時候,師父沒有特別叮嚀,沉默那刻的神態也不會在河面上映現出來。不可思議地,是看到容貌的時候,竟然看到另一個容貌,可以打破時空的阻礙。
畫好慈像,焚香禱謝,感悟地說:「當時幾乎錯會了他老人家的深意呀!」每逢師父忌日,必要設齋紀念,表達無限感念。
遊方的和尚及弟子都會好奇地問他:「雲岩和尚給你什麼指示,讓你開悟呢?」「他什麼也沒說。」「既然什麼也沒說,還尊他為師嗎?況且,南泉師父才是你第一個參禪的師父呀,怎麼不列為他的弟子呢?」
原來洞山從小出家,常誦《心經》,有一天唸至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,突然摸著臉問師父:「我們明明有眼耳,怎麼經典卻說沒有呢?」讓大眾駭異震撼,鼓勵他長大後參襌去。
出訪參襌第一站就是南泉襌師。
南泉是馬祖道一襌師的弟子,以「南泉斬貓」公案震動叢林。道一忌日,南泉設齋紀念,吶吶自語:「不知道他老人家會來臨嗎?」大眾莫名其妙,洞山出口:「有伴即來。」南泉誇他:「這個後生小子甚堪雕琢。」
南泉對洞山誇讚,雲岩對洞山什麼也沒教導,所以大家都奇怪,為什麼洞山卻以雲岩為師呢?
「我尊雲岩師父,不論列道德佛法的高深,主要因他不為我說破。」
禪是佛語心,只是無門關。設關隘而沒有門禁施設,可以策馬而過,為什麼大家卻在關前逡巡不入呢?可見障礙是心裡的,是虛擬的。
達摩祖師東來,一葦渡江,隻履西歸,都是以實際的身影印證大道。不得已,他說有二入:理入與事入。理入就是窮理追源,追查在最初一理的源頭才能豁然貫通;再來是事入,從因緣法中承擔,一直到心行處滅,言語道斷。
祖師的「直指人心」就是承接這一貫的衣缽,違背這無門關的,顯然不是禪宗。
《華嚴經》是法界大法,特別提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,最後到彌勒閣前,瞻仰讚歎,彌勒彈指一聲,樓閣門開,入內但見百千萬億樓閣,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,領諸眷屬併一善財而立其前。
另一善財?又何必見甚多的善財呢?
無情說法,情識說法,相去何止千里?
有一僧舉問洞山:「時時勤拂拭,為什麼不得他衣缽。未審什麼人合得?」
師曰:「不入門者。」
曰:「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?」
師曰:「雖然如此,不得不與他。」
門是法塵,有一理膺胸、一事掛懷都非開悟,所以勉為不入門者得。
可是這樣一答,又落法塵,所以洞山緊接著說:「直道本來無一物,猶未合得他衣缽,汝道什麼人合得?這裡合下得一轉語?且道下得什麼語?」
禪師為破法塵,所以進一步追問。
當時有一個僧人下了九十六轉語都不契,末後一轉,始愜師意。洞山誇他:「為什麼不早說呢?」
這個末後一轉語是什麼:百草頭上祖師意,不與你說破。(註)
恰好有另一個僧人路過,聽到這段異聞,但遺漏了末後一轉語。跑去問這個僧人,僧人什麼也不肯說,三年糾纏,不得回答。
其僧病了,急得不得了,好意相問,不肯答話,不如拿刀相逼,這個僧人悚聲相答:「直饒將來亦無處著。」僧人禮謝,病好了,也開悟了。
本來無一物,道理不難理解,事相難達呀!
意識的見聞覺知心是表面意識,把表面意識停止了仍然是靜態的表面意識,是意識覺知心,不是真心。
宗門所謂「離心意識。參!」甚堪玩味。
耕雲老師說:「掃除有求、有得心、有為、有悟心,時時向內心用功──從反省到不二過;從眾生之所以然到確然自見與佛不別處,便能不落外道,不遭魔擾;便能直養無害,以迄自心圓滿光明,的的見得本來面目。」
這是宗門要旨。
洞山辭世前有一則公案,值得詳參。
師問僧:「世間何物最苦?」
僧曰:「地獄最苦。」
師曰:「不然。」
僧曰:「師意如何?」
師曰:「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,是名苦。」
師問僧:「名什麼?」
僧曰:「某甲。」
師曰:「阿哪個是闍黎主人公?」
僧曰:「見祇對次。」
師曰:「苦哉苦哉!今時人例皆如此,只認得驢前馬後將為自己,佛法平沉此之是也。客中辨主尚未分,如何辨得主中主?」
這個對話,指出一般參禪人認為能見能答的「見祇對人」為主人公,這是驢前馬後的見解,落在意識坑裡,難免墮落輪迴。所以再以「辨得主中主」激勵僧人(弟子)。
僧便問:「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,如何是主中主?」
師曰:「怎麼道即易,相續也太難。」
客是五陰等障,主是自性。一般人只會得意識流動之嘴皮禪,洞山以「你自道取」指示他,他卻又不領會,只在語句流連忘返,盡是客中主、客中客,何能主中主?難怪禪法要相續不絕也難呀!
師示寂,令沙彌去傳話雲居,又曰:「他問汝:『和尚有何言句?』但道:『雲岩路絕也。』」汝下此語,須遠立,恐他打汝去。(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十五)
雲居道膺禪師是洞山的弟子,洞山將辭世,卻派了一個沙彌小和尚去報訊,師徒兩人演了一場禪劇,非常精彩。
沙彌見到雲居,話未完就被雲居打了一棒,倉皇回來,洞山和尚卻非常高興。
雲居棒打小沙彌,既演出了德山棒的神妙,可惜這個沙彌莫名其妙,白挨了一棒。雲居又以這一棒上報師恩──「師父說什麼相續不相續,我雲居絕對可以承襲您教外別傳的衣缽。」
時空遠隔,傳來洞山的吩咐:
「學者恆沙無一悟,過在尋他舌頭路;
欲得忘形泯蹤跡,努力殷勤空裡步。」
折斷了蓮葉,揮一揮綠的清涼,飛雲原來在池底裡,映在水裡,不是不言而自言的容顏嗎?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註:九十六轉語譬喻佈大成道前,印度當時有九十六種學說,但未觸及根本問題,佈大夜睹明星而開悟,這下子才打破謎底,所謂千花競豔,齊向陽光敬禮。
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持
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
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
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
香嚴和尚開悟了,寫了這首偈。
妳說:「為什麼聽到擊竹的聲音會開悟呢?為什麼洞山良价看到水中倒影,頓時開悟,沒有線索呀?」
時節因緣,不可思議。《金剛經》:「是經義不可思議,果報亦不可思議」。
什麼是時節因緣呢?結果自然成呀!頭正尾正呀!
溈山禪師聞偈,高興得很,也可以告慰百丈禪師在天之靈。但是弟子仰山,被稱為小釋迦的年輕禪者,故意向溈山師父說:「沒有當面勘驗,怎麼可以草草認定?」
溈山知道仰山的慈悲,他不是為了勘驗去的,而是為了拉拔香嚴。一個開悟的人,只獲得因地佛的地位,沒有悟後鉗錘,不能獲致果地佛,不能入聖位的。
間關千里,仰山來到香嚴那兒,就說:「既然你開悟了,不如另作一首偈,讓我評評真章吧!」
一位開悟的禪者,隨機印證,直敘心懷的感受就可以了,不必動腦筋堆字砌詞,香嚴隨口吟出:
「去年貧,未是貧;今年貧,始是貧。
去年貧,猶有卓錐之地;今年貧,錐也無。」
這首偈,證明仰山見到香嚴,已是香嚴開悟後的一年了,這段期間,香嚴深得修行三昧,將我執與法執都揚棄得乾淨了,真的成功了。
仰山卻故意對他說:「如來禪許師弟會,祖師禪未夢見在。」我現在可以肯定你會得如來禪,但祖師禪連影子還見不到。
祖師禪本來就是如來禪,如來清淨禪就是自覺聖智,祖師禪亦是自覺聖智,不離清淨如來。所謂祖師禪是在肯定六祖惠能的成就。
六祖不識字,沒有研讀三藏十二部,本著他的悟道內涵,隨口演說佛法,運用的盡是一般民眾的語言,開導禪人,峰迴路轉,急速成就,都是因人施教,不守成規,建立起了活潑生動的中華禪風,雅稱「祖師禪」。
仰山鼓勵香嚴建立起獨特的風格,所以有此一激。
香嚴又頌一偈:
「我有一機,瞬目視伊;若人不會,別喚沙彌。」
若是一位開悟的禪者,在接機開導示人的時候,不可以在語言文字上推敲,只在揚眉瞬目中以心印心,端賴時節因緣。
仰山這時候高興地說:「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。」
上段也是一則公案,發人省思,不可當做記事而已。
香嚴是自悟,在擊竹的時節因緣上開悟的,真不可思議。然而,自悟而不自知,才是一場春夢,讓絕好的機緣消逝掉,甚至嚇出冷汗呢!更可惜的是開悟後不知如何修行,蹭蹬不前,進進退退,還是一場春夢。
所以,印證及鉗錘,都需要明眼的善知識從旁點撥,禪門重視師徒關係,就是這個原因。仰山慧寂到香嚴那兒,除了印證香嚴的悟境,重要的是讓他修行走對方向,才演出這場精彩的對話。
文字只有幾個字,但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磨鍊,不是一下子就讓香嚴達到至境,這裡才能體會到仰山的慈悲心腸,也才能印證師父對弟子的苦心。
圓悟禪師:「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,然後放下複子,不論歲月,用做事綿綿相續,不怕苦硬難入,參取管須徹去。」〈示瑛上人〉
真的,香嚴太幸運了!
遺憾的是明眼宗祖難得駐世,世人亦認不得他,排斥他,大家反而重視發言盈庭的人,為他們廣建梵宇,視為不可多得的大師,這是禪門寥落的可悲,也是人類心靈下降的突顯。
就以雍正皇帝為例吧!從文治武功上論,他的成就豈非佼佼者,對禪宗的愛護也顯得不可多得,他尊崇佛教,顯密並重。
然而就因為太聰明了,把禪宗當著理論,寫下了「雍正三關」的妙文,廣為時下叢林流傳,不少禪客還把這段文字當著至寶,研發至極,實在無言以對:
「不掛一絲,前後際斷,曰初關。山者山,河者河,色聲香味觸法,盡是本分,無一物非我身,無一物是我己,色空無礙,獲大自在,曰重關。家舍即在途中,途中即在家舍,行斯、位斯、用斯,如是惺惺行履,無明執著,自然消落,曰末後牢關。」
從每一句研讀,你會震撼在他的玄理意境,「無一物非我身,無一物是我己」看來多瀟灑,大自在!然而為什麼雍正朝,卻是翻風覆雨,讓千萬民驚悸的威權時代呢?行不符言,言行相背,從德政上論已不足取,遑論禪道?
就禪道而言,這種三關的論斷,已經背離了「直指人心,見性成佛」的基本精神,盡在文字上玩花樣,而且彼此矛盾,外表是龍袍,裡面裹的是棉絮嘲弄自得的悍漢,卻有那麼多的人把它當著重要開示,列存論文上討論,真是擺尾擺到爛泥塘去了。
難怪香嚴會開個玩笑:「若論此事,如人上樹,口銜樹枝,腳不踏枝,手不攀枝,下忽有人問:如何是祖師西來意?不對他,又違他所問;若對他,又喪身失命。當這麼時,怎麼生即得?」
這種禪門無法大開的事實,自古至今都一樣。要向他說道理,道理非禪;要不向他說,他可不能悟解心開。但是,明明在這兩難之間,也明明說得夠透了,學人偏又不會,總死不了心,掩不了情。
怎麼辦呢?書空咄咄!
當時虎頭招上座強出頭,出眾說:「樹上即不問。未上樹時,請和尚道!」香嚴聽了哈哈大笑!
世上這種聰明伶俐漢太多了,香嚴也只能哈哈大笑,無可奈何,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,為賦新詞強說愁。要是我,拚著命也要踏你一腳,不然撃掌三下,看你當下是不是個人才!
再不悟也沒辦法了。
《論語‧子罕》有一段孔子的教戒:「吾有知乎哉?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,空空如也,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禪師沒有一法予人,只在叩其兩端而竭;如果有一法可說,一理可立,傍門依戶,絕對不是禪宗應有的規範。
秋風掀葉,簌簌聲中,一股無奈升起,淡淡地,靜靜地,無絃之琴難彈,無絃之音難聞。
藏傳佛教隨著達賴喇嘛的出走而廣為世人注目,因緣法真的不可思議,一個動亂造成一個法的波動,不是人為力量所能掌握的。
藏傳佛教傳入西藏地區時,西藏沒有文字,況且地形特殊,高山崇嶺,交通不便,聚落分散,因此,以偈頌歌唱的方式傳達教義是最好的方法。
歌唱必須平民化、音韻化才容易傳播,運用簡易的詞句,很接近原始佛教的味道。看看天馬行空的蓮花生大士,隨心唱著「無染覺性、直觀自行解脫之道」,那種瀟灑自然的神態,隨著歌聲燙平了熾熱的心境,清淨的覺照抬頭,深奧的道理變成柔軟的泉水,洗滌著行者的道心。
現在的人喜歡在莊敬華麗的殿堂裡,運用深不可測的玄理說明佛教,採用的語言都是千年以前的詞彙了,講者與聽者彼此覺得非常生疏,在一片模糊的概念中隨著抖落了精神本身的昂揚。
我反而偏愛古代聖哲,站在草原上,以清亮的歌曲,演唱偉大的道理,彼此親切地呼應著,道理貼近人情、自然之道。
有時候,諷頌著《金剛經》,在無思無惟中,大唱著:「一切有為法,如夢幻泡影,如露亦如電,應作如是觀」,在這種虛而不實的感覺中,再諷頌著:「若以色見我,以音聲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見如來。」反覆地唱著,勝談一部浩瀚的《大般若經》。
二千六百年前,如果沒有牧羊女隨興的歌吟:「太緊了,音僵;太鬆了,音懶。不緊不鬆,音美妙!太緊了,音僵;太鬆了,音懶。剛好、剛好,音美妙!」佈大緊繃的心絃怎麼能放鬆,自然怡和地坐在菩提樹下,讓智慧集中呢?
佈大悟道,悟了因緣法,因緣法是一座應和萬法和諧的絃琴,讓天道、人道都能在中道中運行。
縱然佈大出道,他所運用的語言也是當時印度最普遍的語言,不可能為了佛教再創造一套離開世俗的語言。我們看《華嚴經》、《楞伽經》等等,在某段落之後,一定會加上偈唱,才能廣泛傳播。
西藏的聖者承襲了這種無瑕的熱情,他們放情歌唱聖道,響徹雲霄,顯得純清而且曠達。《米勒日巴傳》也留下了很多的唱詞,甚至於米勒日巴一生的事跡,都可以偈唱流傳,多麼貼心的佈道方式啊!
例如米勒日巴尊者就擺脫了神秘面紗,在歌唱中直接說出了佛法只在一心,這個心就是密法:「無來無去無所住,三世平等一定性,心中無有生死因,本來清淨如空空……最深法寶對面來,心中母子親見面,倘若母子不相逢,棄清淨身又入胎。」
想想看,在原野上歌唱佛法,還能有什麼儀式、禮拜、護摩等等嗎?
離開人世之前,他勸我們:「卑處持著頂上到,緩緩持則快快到,……空心若得大悲生,大悲生時自他無。」真情流露,真法流盪,與禪宗的作略相比較,實在非常有特色呢!
佛教傳入中國,剛好是魏晉南北朝的時候,中國社會被世家門閥所壟斷,他們用的是和一般平民百姓不同的貴族語言,甚至不玄就不是上流社會,所以玄學盛行。
那時候的音樂也是沉悶、低啞、壓抑性的,如果沒有陶淵明的出現,還會以為那時候的人沒有音樂或文學細胞呢!
佛教經典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出來了,用的是貴族的語言、士大夫的語言,偈頌也失去平易近人的意調,沒有清朗的歌唱了,落入了混沌的讚偈,與本文相較,反而更難懂。
直到六祖,他慧眼獨具,在每品的結束前,簡要的偈頌回復了平民化。像:「生來坐不臥,死去臥不坐,一具臭骨頭,何為立功課?」簡潔得比任何格言還親切。
他對法達的偈頌:「汝今名法達,勤誦未休歇,空誦但循聲,明心號菩薩。汝今有緣故,吾今為汝說,但信佛無言,蓮花從口發。」更是貼近心肝。不但詞句簡潔明白,一股親切的感情,在師徒兩人間激盪,我們在諷頌時,也覺得很親切受用呢!
想起孔子,他的教學方法,不就是在這樣和弟子毫無阻隔的交流中展開的嗎?難怪孔子得有七十二賢人,六祖一花開五葉,因為他們都是生活在一般人的生活裡,懂得他們的語言、懂得他們的生命。
耕雲老師,是一位運用當代的語言闡發禪道的智者。將經典濃縮,簡要而有體系,當代幾位傑出的智者還可以辦到,而且也受到社會的肯定;但是大膽地運用一般平民化或日常化的語言,將經典衍化的就只有耕雲老師。
遺憾的是因為太現代話化了,有些人反而認為不夠深奧而棄之不顧,棄金擔麻,徒呼奈何!
另有些人不懂得耕雲老師的苦心,應用現代的語言詮發禪的真精神,就是要落實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,不是要形成理論化的顯學,所以他始終沒有建立特有的門庭設施。
另一方面,他知道歌唱的可愛,不但容易記憶,而且唱者容易感情投入,所以請黃友棣教授或其他禪德作曲,大量發表禪曲,隨各根器而諷頌。
像〈廬山組曲〉一曲,無論水邊林下、高山大海,都可以引吭高歌,投入無邊無際的音域裡,讓自性引領。
又如〈無心法〉,如果在原野上品味,體會自覺的各種向量,有時以心觀境,有時以境陳心,有時心境合一,有時心境相泯,妙不可言也。
最後,熱淚盈眶地唱著他慈悲的「叮嚀」,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:
往事渾忘卻 勿慮亦勿懼
秒秒持安祥 涵泳逍遙裡
堅守獨行道 交往簡為宜
己溺難救人 專心己躬事
事事皆因果 不干他人事
速自淨己眼 正邪當辨取
百死餘孑者 何憂復何懼
老子豈不曰 患為身而已
身心原是幻 愚者執而迷
勿似愚痴漢 臨歧徒從歧
心若不動搖 鐵輪旋任伊
宋代禪師文采豐富,心光灼爍,馳騁在佛教叢林中大放異彩,很多士大夫也景然從學,鐘鼎山林彼此唱和,那種景象實在美不可言。
影響最大的是理學的興起、道教的性命雙修,對生命學做一番重新的闡述,甚至可以大膽地說:中國化的佛教於焉誕生,禪變成中國佛教的主流。
其中,楊岐方會、五祖法演、圓悟克勤及大慧宗杲等四大禪師,衣缽相襲,四代傳燈,對禪的發揚及貢獻非常大,直到現代,子孫遍滿寰宇,為臨濟宗開萬代基業。
研究禪學或者志心參禪的人,一定要把這四大禪師的行誼,做一番深入的研究,並且體會出臨濟宗直說直破的大膽作風,才不致於落筆空疏,立論稀鬆,誤導參禪的正途。
大慧宗杲舉參話頭,是為了導正參禪的偏頗,等於糾正我們參禪的錯誤,所以他的書信合成的尺牘,是立志參禪的人必讀的,以便建立正確的見解,對現代的學人一樣重要,不可忽視。
《圓悟心要》則比較適合開悟的人,於保任一段時間以後參閱,從中獲得智慧,步步昇進。如果一位禪師在指導弟子進學的時候,不能運用本書及《六祖壇經》做為本據,是否可以列席禪座,實在令人流下冷汗。
我又把中華禪學雜誌社出版的《耕雲書箋》,合併研讀,日積月累,領會得春意盎然的喜悅,才知道祖師心的偉大,透過文字,會湧現陣陣心光,掃除積學的困惑,出現一種難以描繪的溫暖與寧靜。
圓悟禪師在寫給一位長老的信(普賢文長老)中,很懇切地說到他開悟的經過,要參禪的人避免他的錯誤,值得我們詳細參研:
「老漢昔初見老師(五祖法演),吐呈所得,皆言裡耳裡機鋒語句上,悉是佛法心性玄妙,只被此老子舉乾嚗嚗兩句云:『有句無句,如藤倚樹。』初則擺撼用伎倆,次則立諭說道理,後乃無所不至,拈出悉皆約下,遂不覺泣下,然終莫能入得。
再四懇提耳,乃垂示云:『你但盡你見解作計較,待一時蕩盡,自然省也。』
隨後云:『我早為你說了也,去!去!向衣單下體究,了無縫罅。』因入室信口胡道,乃責云:『你胡道作麼?』即心服。真明眼人透見我胸中事,然竟未入得。
尋下山,越二載回,始於『頻呼小玉元無事』處桶底子脫,纔始覷見前時所示真藥石也,自是迷時透不得。」
這段自述指出了參禪悟道的要點:
第一、不要以為任何道理說就是禪,這是自己胸中的見解,人人都有見解,禪豈不變成理論,形成一股學問了嗎?
第二、不要誤以為摒棄見解,一切皆空就是襌。也不要以為身心的各種變化,例如輕安、見光、禪樂,停止想念就是禪,那是把玩光景,入空相,其實還是有個空的相。有相有得那不是禪。
第三、他的開悟,是一句「頻呼小玉元無事,只要檀郎認得聲」發生疑情,走下台階,看見雄雞飛上欄杆,引吭高鳴,一聲明歷歷中親證「元無事」的平靜心境。這是心靈的一種特殊的震撼,而不是道理的了解,道理的了解只是「認得聲」,不會產生深刻的震撼。
洞山過水、香嚴擊竹、靈雲見桃花等等是祖師禪傳達的特色。如果拿道理、學問當禪,打坐到一念不生、入定寂滅,或觀照身心變化、見師見光,甚至獲得神通變化等等,都是「有句無句,如藤倚樹」,有一天樹倒藤自枯了,因為這些東西都必須仰賴色身為基礎,沒有色身時,講什麼道理?打什麼坐?如何神通變化呢?
宗門初關是破參,是見性,是頓悟,實證般若!修行就在保任般若,全彰般若,全生命都一般若!所謂「藤枯樹倒」,一法不立,一理不存,前後一貫。
什麼是見性?
《金剛經》有句:「是經義不可思議,果報亦不可思議」,這個不可思議就是見性,非文句可以描摹,所以進一步又說:「無我相,無人相,無眾生相,無壽者相」,連時空的感覺都打破了。
虔誠讀誦《金剛經》,不加思繹註解的,可以證般若而見性,代有所聞,真實不虛。因為《金剛經》為佈大親身所說,一直保持著「為人演說,不取於相,如如不動」,在法身說法中,有緣的自然身心脫落,這是《金剛經》的殊勝處。
這是金剛印心。
見性就是開發我們本具的金剛心。
假如心境沒有「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相」的「不思議」狀態,就沒有般若,沒有金剛心,縱然有千言萬語的原理,或者各種玄妙的心身變化,都是鬼家活計,與法無關。
六祖大師於賣柴時,聞客誦《金剛經》而開悟,這是震鑠古今的大事。有些人認為這是「解悟」而不是開悟,爭論不休,關鍵是這些人沒有開悟,不知開悟的特殊心靈感受,不相信聞誦《金剛經》會開悟。
為什麼六祖這時開悟,以下有幾點證據:
第一、六祖不識字,又不識《金剛經》,如何生解?這是聲陀羅尼喚醒六祖的自性,所以聞經,心即開悟。
第二、開悟後安頓母親的生活,起程往湖南的五祖寺即東山寺,如果不是心靈受到極大而且深刻的感受,不會立志這樣堅定,萬死不辭。
第三、六祖一見五祖便說:「惟求作佛,不求餘物」,又說「佛性本無南北」,見識之深,志趣之宏,如果不是見性,怎能背負這種恢宏大量的氣度?
第四、本來五祖要他隨眾作務,學為儀規、禮佛、聽經等等,六祖直言:「弟子心中,常生智慧,不離自性,即是福田」。可見他見道很深,沒有滲漏的片刻。
至於後來五祖三更講授《金剛經》,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大徹大悟,則是果地成熟了,豈只是一般的開悟。
佈大在菩提樹下證道,讚嘆:「奇哉!奇哉!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,只以妄想執著,不能證得。」開啟了佛教的偉大事業。
佛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差異點就是證得自性般若。
每人都有相同的智慧德相──般若,這個般若也只有經過一番的努力才能證得,不是理論上的空。這個毛病,反映在現在佛教的衰敗,到處都是學術論文,把這些論文編製成冊,保證比原有的《大藏經》多。
但他們有沒有證得般若?天曉得啊!如果真的證得般若,努力修行都怕時不我予,怎麼會浪費時間在撰寫論文呢?
舉德山宣鑒悟道公案,就曉得這事重大。
德山宣鑒禪師本來講演《金剛經》,獲得很大的名聲,還將《金剛經》加予註解,讓人可以研讀啟發智慧,所以他自豪:「一毛吞海,海性無虧;纖芥投鋒,鋒利不動。學與無學,唯我知焉!」真是意氣風發,大家尊他為「周金剛」。
後來他聽說禪宗可以「教外別傳」,完全「不立文字」,即沒有什麼教理,所以氣得走出四川,要到湖南澧陽與龍潭寺的崇信和尚做一場辯論。
走到澧陽路邊,向一位婆子買餅吃,婆子問他:「過去心不可得,現在心不可得,未來心不可得,請問和尚點的什麼心?答得,免費供養;答不得,請到別家買。」
德山一時傻了眼,答不出話來。
為什麼?因為他只在文字上講求道理,不能親證三心不可得的自性,婆子一問,找不出答案。這種情形,和香嚴被溈山靈祐問:「什麼是你的本來面目,答一句來!」就啞口無言一樣,沒有親證般若,遇到實際問題,自然答不出來,禪宗所謂沒有轉身一路。
因為他們在語言文字追求道理,人家問的又非什麼道理,他們怎麼不昏頭暈腦?
德山上了龍潭寺,依附了崇信和尚。崇信依然保持平日的風格,做些朝示晚參,白天有時講些公案,幽默地答覆問題,晚上開放方丈室,讓參禪自認有心得的人來印心。
有天夜晚,方丈室寂寥,德山辭歸,崇信點了紙捻子照明,德山接手,準備反身出室,崇信突然吹熄了火捻子,倏明倏暗中,德山親證了不可思議的心靈變化,開悟了。誠誠懇懇地拜謝崇信,感恩地說:「從今以後,再也不懷疑天下老和尚的舌頭了!」
天下老和尚經常掛在口頭上哪個字?這個字說來輕鬆,如果沒有這一番刻骨銘心的心靈震盪,這個字就沒辦法與血肉身融和在一起!修行也是把這個字在自己的身心上融化而已。
第二天,他當眾把他心血結晶的《青龍疏鈔》──《金剛經》的註解,一把火燒成灰,然後說:「窮諸玄辯,若一毫置於太虛;竭世樞機,似一滴投於巨壑!」任何理論都是隔靴抓癢而已。
如果他下山碰到那個賣餅的婆子,婆子還問他同樣問題,他會如何回答呢?
試著給你一個答案吧!
他會拿起餅,並且向婆子深深合什一禮,說:「謝謝供養!」這個婆子會再供養一杯豆漿,因為三心不可得,你如果偏要在這個問題繞圈子,何時有個三心不可得的歇場呢?
六祖聞客誦《金剛經》就見性,是不是單獨的特例?不是的,我們可以從南懷瑾的《金剛經說什麼》這本書的序看到這一段描述:
「《金剛經》的感應力非常大……,每天練拳運動以後,首先唸《金剛經》……,反正人家告訴我唸《金剛經》很好,我就唸《金剛經》……,有一天,我唸到『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』,忽然我覺得我沒有了,我到哪裡去了?不知道啊!……後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」
南老是當代的禪者,他專心唸《金剛經》而見性卻不知道,後來才恍然大悟,比之於六祖,他是後知後覺,未能當下證悟金剛心,但仍然是一位福德因緣很好的人,也為我們證明,只要如法持誦《金剛經》,也有機緣明心見性。
什麼是如法持誦呢?
耕雲老師在〈禪、禪學與學禪〉一文中說:
「真正受持《金剛經》,從頭到尾要讀誦出聲,聲音或大或小,但不能默唸,要沐浴、更衣、漱口,最好是清晨,精神好時可以一口氣唸三遍,唸完了把經卷一合,看看自己的心態有什麼覺受,不要向外看……佛法講覺,講正受,都是重視心的覺受。你把唸經的覺受,感受得清清楚楚,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,然後把它保持住。」
誠敬持誦,障輕的人,見性速;障重的人就要堅持不輟,並且配合反省懺悔,也有見性的日子。這是佈大廣大無限的慈悲憐憫,隔著時空一直護持著我們,我們應該頂禮領受。
耕雲老師又在〈禪的認知與修學〉中點出:
「《金剛經》的可貴,在能給予人一顆八風不動的金剛心;金剛心的可貴,在能使煩惱不侵入、妄想不萌生,如如不動,安祥自在。」
所以他讚嘆:「這部經真是太好了!太殊勝了!可說是禪者的無價之寶。」
六祖也這麼叮嚀又保證:「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,即得見性。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,經中分明讚歎,莫能具說。」
如果一邊唸,一邊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,自己講給自己聽,這樣只是讓自己的七識心田翻風起浪,怎麼也不能相應。
例如德山宣鑒和尚,未開悟前善解《金剛經》,博得「周金剛」的讚譽。但在崇信和尚那裡參學,這些學問解決不了生死問題,因為他對《金剛經》的註釋──《青龍疏鈔》,只證明他滿腹的佛學而已,一點也起不了金剛心。
更深夜靜,崇信借著紙捻子的遞出與吹熄等動作,瞬間讓德山親自體驗了金剛心,才知道佛法不是說的。開悟以後,他即刻把多年的心血結晶──《青龍疏鈔》,點著火一起燒掉了,不願意讓七識心田興風作浪,不見性怎麼能刻骨銘心地知道法離語言文字呢?
他為什麼燒掉《疏鈔》?因為見性以後,才知道《金剛經》的句子就在描寫這個心境,就在鼓勵以後怎樣修行才走對路。對沒有見性的人講,他們永遠不會明白,永遠找不出符合點,正像沒有開悟的人讀誦《金剛經》,霧煞煞,『什麼是什麼又不是什麼才是什麼』讓人糊塗。所以不懂的人看《金剛經》,就像一個水桶的水,倒進另一個水桶,又將那桶水倒過這個水桶,翻來覆去而已!
另外,《金剛經》的結構也很特別。一開始,整個前文只在描寫佈大四大威儀的從容自在,「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,入舍衛大城乞食……洗足已,敷座而坐。」
誦這段經文,我們自然會浮現佈大悠遊自在的安祥身態。他和一般弟子一樣,穿好外出的衣服,修飾儀容,沿家托缽,不會揀擇哪家豐盛,哪家是貴人,隨緣隨喜;回到精舍,吃完飯,親自洗好缽具、雙脚,然後敷座而坐。
太平凡了!太一般了!這就是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的具體表現,也是一顆金剛心自然流露的安祥美好,那就是你我共同的生命屬性。
浮現這幅美好而安祥的畫面,我們的心自然地沉靜了,自然安祥自在了,我們不是已經獲得本有的金剛心了嗎?
此外,哪有什麼佛法?何必心外求法?
講說《金剛經》,一律就在這種精神中隨立隨破,一再一再地提醒我們不要著外相,多麼簡單明白。
最後,他老人家還唱起歌呢,多瀟灑呀!
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
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
禪宗重視以心傳心。
晚參的安排是適應「印心」而設。開悟或見性,即是弟子的心地與祖師的心地一樣的證明,並不是要聽聽弟子開悟的道理。
靈山會上,佈大拈花示眾,迦葉會心微笑,就是以心傳心,所以佈大說:「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,汝當護持。」這是禪宗的由來。
五祖弘忍大師對六祖說:「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,人未之信,故傳此衣以為信體,代代相承,法則以心傳心,皆令自悟自解,自古佛佛惟傳本體,師師密付本心。」傳心源遠流長。
傳心的內涵,沒有見性的人無法想像,故向來都嚴禁說破,這是為了不妨學人開悟。如果說破了,學人似懂非懂反而容易「誤認」為真,塞人悟機。
耕雲老師在不得已中,以近代科學知識,勉為其難說破:
「每個生命都有磁場,這是現今科學家所公認的。現在營養學專家已經發現食物中含有光子,因為凡是物質都有電子,有電子就有游離現象,當電子消失的剎那,它就發光,而人的色身也是物質,人的生命卻極甚奧妙,不可思議……。
一個有成就的人,是把生命的雜質完全淨化了,他會有強烈的光的半徑,當你進入他的輻射半徑,心就好像光合作用而被同化了。被同化的感受就是定……,此時心念停止,一片清明,說話不必思索,脫口而出;雖然脫口而出,絕非語無倫次,但是心裡就是沒有動念。」(《中華禪風的演變》)
心心相印,師徒之間融合為一心,心心不異,因為每個人性情不同、人格不同,只有傳心才能夠像蓋印一樣,蓋一萬個都相同,這就是禪宗以心傳心的祕密,沒有大成就是無法傳心的。
當初佈大宣示大法的時候,就經常以心傳心,讓弟子心窩發熱,觸動本心,自然流下熱淚,同時沐浴在一片祥和的心靈狀態中,真是殊勝啊!
《指月錄》也記載了很多以心傳心的公案,歷來沒人說破,姑試引證之,願皇天不以粗鄙見責。
二祖斷臂求法,表示願以生命投注。
達摩初祖知為法器,向他說:「諸法印,非從人得。」
二祖說:「我心未寧,乞師與安!」二祖生死之心未了,忐忑不安,特來求法。
初祖:「將心來,與汝安!」
二祖良久說: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
初祖:「我與汝安心竟。」
為什麼二祖覓心了不可得呢?原來初祖傳心,要他把握住這時刻的心態就對了。
馬祖道ㄧ禪師也經常傳心,最特別的是與石鞏慧藏的因緣。
慧藏本來是個獵人,有次逐鹿從馬祖庵前經過,問師是否看到鹿奔馳逃過?
馬祖故意問他:「你解射否?」
慧藏說解射。
馬祖就問他:「你一箭可射中幾隻鹿?」
慧藏說:「一箭射一隻。」
師向他說:「這麼說來你不解射藝。」
慧藏不服問師:「你一箭射幾隻?」
「一群。」
慧藏嘆氣:「都是有靈性的,為什麼射他一群!」
師再問他:「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,何不自射?」
慧藏摸不著頭緒:「教我自射,直是無下手處。」
師曰:「這漢曠劫無明煩惱,今日頓息。」
慧藏獲得大法,馬上放下弓箭,從師出家。
這個公案,當馬祖向慧藏說:「這漢曠劫無明煩惱,今日頓息」就是以心傳心,慧藏有慧根,即刻領悟,所以出家了。
楊岐方會未悟前,在慈明座下,總是幹最辛苦的總務,忙來忙去,參不了禪,每次咨參,慈明總是勸他多關心寺務,不急不急。有時候,慈明會向他說:「你將來兒孫遍天下,不用忙著參禪。」
楊岐方會心裡不舒服,心想在您座下辛苦做盡,卻得不到佛法,他就趁慈明外出的機會,事先在山道前方等著他。看到慈明和尚來了,捉住責問:「今日一定要說明白,不然打你一頓。」
慈明不慌不忙地說:「你知是般事便休。」楊岐馬上拜倒於泥途上叩謝不已。
什麼是「知是般事便休」呢?就是傳心的心態,一下子就讓楊岐方會見性了。方會也不糊塗,不讓它交臂而過。
我們再看禪宗第一公案,惠明趁及六祖,本來想拿取衣缽,轉而向六祖求法。
六祖要他摒息諸緣,一段時間後,向他說:「不思善,不思惡,正與麼時,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?」惠明言下大悟。
若非傳心,何能如此容易見性?
所以六祖又再叮嚀他:「與汝說者即非密也,汝若返照,密在汝邊。」開悟後保任觀照,時時提撕,就是密行。
從以上幾個公案,說明偉大的智者,都有強大的傳心力量,在他的般若智照下,聞法的人當下妄念全消,一片空朗,然而字字明白,事後卻又一句不存,只存在著生機通暢的本來面目。
傳心是極為難得的機緣,說來非常神祕,所以祖師不明言。而且弟子是否能領受、自肯、自悟、自解,又是一段很長的路呀!
秋天的黃昏顯得特別地清涼,北回歸線的特殊性地帶,時常會飄著絲絲的雨花,西天還透著一大片的銀黃色的彩霞,而射日塔正前方,會突然出現一道七色鮮爛的彩虹,長長地跨過天際。
你說到蘭潭看彩虹,那才是彩虹的故鄉。
哦!你要看的彩虹,是湖底的彩虹,它會在湖面的波光中倒掛,天與湖相連,是不是一個奇妙的組合?另類的懸想?
而我愛的是漁戲彩虹,是漁翁垂釣的彩虹,在蘭潭波光中闢出一個世外桃源。
於是緩緩地踏著油門,讓車子在山子頂的大雅路上爬行,西風微涼,雨絲飄著,平靜的心似乎貼著車子的引擎,緩緩地開著。
透過這種自然的聯合,我們似乎連結在一起了,聽得到車輪碾過路面的節奏,穩定的節奏中呈現著祥和的應和。
原來車子和我們是一體不分的,但必須透過不躁不急心緒的操作,瑜伽就是聯合,生命的聯合,祥和就是瑜伽呀!
不僅車子和我們是一體的,再加強安祥的深度,憬然發現,整座山、整塊湖、車子、心和身體,緩緩地構成一個不可分離的生命體呢!
那是以前沒有的經驗。
一種奇妙的微醺的感覺襲上心頭,趕快把車子停下來,因為這種微醺的感覺,覺得車子在操控我們,而不是我們在操控車子。
離開車子,踏著湖坡,身上輕飄飄地,似乎著不了一點力氣,像一個充滿氧氣的氣球,東盪西晃。你突然大聲地叫著:「找到了彩虹的故鄉了,在湖底深處」。
湖底真的有一條長長的彩虹,落在層層的翠綠波影中,深深向下延伸,延伸又延伸。抬頭望著天上的彩虹,低頭望著湖中的彩虹,頓時有一種分不出真實與虛幻的感覺。
天上的彩虹是真的,但似乎遙遠多了;湖底的彩虹是虛幻的,但似乎親切多了。
有多少人會像你這樣,異想天開地跑到山上的湖泊看彩虹,看湖底的彩虹?
你撥動著湖水,晃晃盪盪中,彩虹也在漣漪中晃動著,仔細看,是動而不動的,不動而動的,真的太親切了!
原來彩虹的故鄉,在你奇思異想的湖泊裡。
西風送來雨絲,西天是燦爛的黃昏,一個橘紅的落日掛著遙遠的天邊,你突然唱起歌:
嫩綠的小草啊,在風裡抖顫,也有它的故鄉。
晶亮的小星啊,在天際隱微,總有它的故鄉。
而彩虹啊!你的故鄉在哪裡?西風呀!捎個信,讓它在夢裡告訴我!
彩虹是天際的歌,無所從來亦無所去,拋下絲綸,釣那湖裡的彩虹吧!漁戲荷葉動,垂絲萬里虹。
垂絲深潭,獨釣彩虹,卻跌入千古的回憶,那是垂絲深潭,獨釣錦鯉。
回憶是輕愁,輕輕地籠上心頭,晃動著船子和尚的淡漠,其實內心澎湃著法的熱情,菩薩低眉,浩蕩為何情?
船子德誠與道吾及雲岩都是藥山惟儼禪師的弟子,三人成道之後,打算個別找個棲息的道場,繼承禪的法席。
臨別依依,德誠向二位師兄真誠地告白:「您們都知道,我生性疏野,雅好山水,要我坐道場開演佛法,那種拘束我過不了的。將來您們如果碰到一位伶俐漢子,推介給我,讓我造就他,以延續法脈,並且報答師父的栽培,就感恩不盡了」。
雲岩禪師造就了洞山良价,開闢出曹洞宗的天地,前文已提過。道吾宗智的弟子石霜慶諸,得法之後,卻隱遁在長沙瀏陽的製陶家,當個製陶的師父,過著淡泊的生活。後來,洞山才把他誘出,成就一番禪林勝話。
德誠是和尚,到了秀州華亭,就在河邊租條船,自己當起搖櫓渡口的船伕,接送渡客,高蹈潛隱,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得道的高僧。
我們把這些小小的細節提出來,僅僅提供讀者了解,禪不是孤立於寺院的學問,也不應該有任何形式的拘束,而是生動活潑地存在於實際的人生的。
如果我們不把船伕德誠、陶工慶諸形象化,呈現在我們面前的,不是一張張可愛又憨厚的臉孔嗎?
這一股潛沉的精神,漸漸地滲透到民間,使禪變成人民生活中常用的醬料,處處讓人的精神有舒解的要方。可惜,這股禪風,在蔽塞的社會環境中,被邊緣化。
道吾有一天到了京口,聽說有一位夾山和尚佛法精深,就去崇寺裡邊聽。
有個僧人起身向夾山問法:「如何是法身呢?」
「法身無相」。
「如何是法眼?」
夾山說:「法眼無瑕」。
道吾不禁失笑。這一聲笑,讓夾山一愕,隨即下座向道吾頂禮,並誠懇地說:「我的回答一定有錯失,請和尚慈悲,指出缺點,讓我精進」。
道吾笑而不答。
夾山再三請求,道吾仍然笑而不答。
夾山客氣地請問,道吾就賣個關子:「要我說破也無法讓你了解,不如去問那位船子和尚」。
「這位和尚有何勝處?」
「上無片瓦,下無卓錐」。
道吾聽夾山說法,簡要明確,是一位僧材,但始終落在義理上,無法在生命中開花結果,所以失聲一笑,測試他的涵養如何。
好個夾山,馬上下座求教,一點也沒有派頭,道吾有意成全,指示他去拜會船子和尚。
船子看到一個和尚來拜會,開口就問:「大德在哪座寺廟修法?」
夾山答:「寺即不住,住即不似」。這是禪語,看來頗有禪風。
船子再問:「不似,似個什麼?」
夾山:「不是目前法」。
船子不以為然:「你從哪裡學來這些文學禪?」
夾山:「非耳目之所到」。
這一段對話,看來都煞有介事的禪風,外行人一聽,必然會陷入玄想中鎮懾了;可是船子是得法高僧,哪裡看不出這裡比量的識見?因為禪是現量的心靈狀態,隨語而轉的義理,呈現出了夾山在文字上糾纏不清。
所以,船子嚴厲地責問他:「你不知道,所謂『一句合頭語,萬劫繫驢橛』嗎?有一法可得,這一法就讓你萬劫死在句下呀!」
夾山無語。
船子停了一陣子,向夾山問:「垂絲千尺,意在深潭,離鉤三寸,子何不道?」
夾山打算開口,就被船子用划板打落水裡。夾山剛手攀船沿,透水而出,船子就逼問:「快回答,快回答。」
夾山想開口,又被打下水中。
這一瞬間,夾山開悟了,也不開口回答了,只點頭三下。
不要以為夾山悟了個什麼道理。夾山在打下水,那裡驚悸中哪有思考道理的空間?只有在生死的沖擊下,那個船子和尚讓他親自體會到生死一瞬間的萬般滋味,只有什麼才是真滋味呢?
那才是「非耳目之所到」呀?
祖師心哪有不希望弟子成道的呢?
想起死心和尚對黃庭堅,那種嚴厲的問話:「黃庭堅學士和我死心和尚去世,燒成兩堆灰留世,我們在何處相見呢?」
想起雲岩禪師,當洞山要離開的時候,輕輕地說:「我百年之後,還能讓你相見,也只是剛才沉默的這個」。
船子把夾山打落水,划板子就是佛法,這就是「直指人心」的禪風,哪有什麼蹭蹬磨菇的道理?
網站維護:張曉鈴,陳翠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