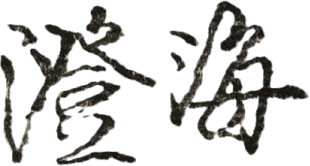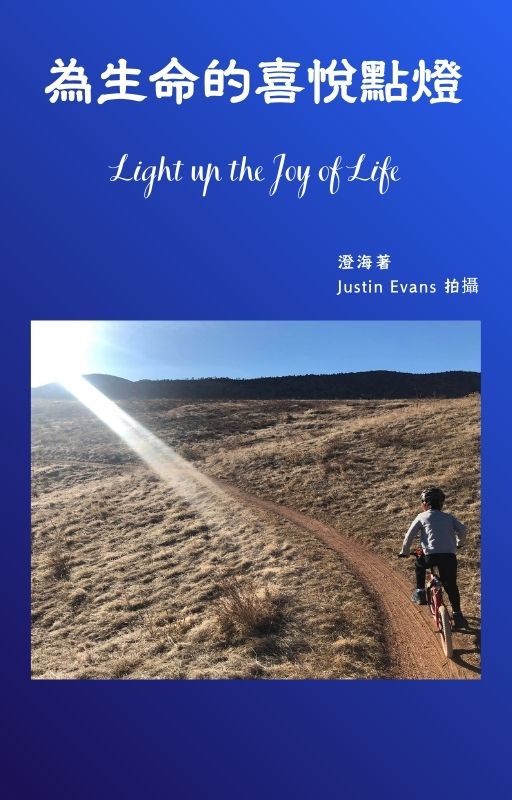廿九、無身中出身
從相對意識轉換為絕對意識,意識仍然存在,不是無察無覺的枯木寒岩,不然如何「開悟」?這是禪法的基本:直指人心。瞬間即讓學人從相對意識轉換為絕對意識。
圓悟克勤說:「衲僧家句裏出身,蓋提持向上機,於無句中出句,於無身中現身,言語道斷,心行處絕,等閑蕩蕩地放曠寬閑。才有機緣,即蓋天蓋地,所謂『密密綿綿,無間無隔』。不是強為,任運如此。是以『諸天捧花無路,魔外潛覷不見』。直得恁麼行履,自然超諸三昧。」(《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.示有禪人》)
禪絕對是言語道斷,運用相對概念所呈現的只是相對概念,說是就有個不是在襯托,說美就有不美的對照,概念永遠引發概念,概念相隨如江水滔滔不絕。有位教授很好意地對我說:「澄海!你寫禪要學術化啊!要有論文的規矩啊!不能隨意。」
語言可以達道,那就是三論宗、天臺宗、華嚴宗,體系非常完備,尤其唯識性相宗,從生死輪迴到萬象森羅都講出來,為什麼還要有禪宗?
禪宗就是要打破這些理論架構所呈現的不痛不癢的相對概念,而直接呈現絕對意識,只好運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,讓雷聲振耳欲聾的頃刻突出絕對意識,這才是「於無句中出句,於無身中現身」,蓋天蓋地,呈現絕對的全體。
禪宗有個公案:則老問青林:「如何是佛?」對云: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則老禮謝,因為誤以為:「丙丁屬火,丙丁童子求火,即火童子求火。我是佛子,何用問佛?」心中篤定了。這是將佛法當道理解會。
我們經常聽到出家人說:「放下一切,放下貪瞋癡。」其實有兩件事放不下:放不下成佛,放不下西方淨土的執持;另一方面放不下面子,隨口放下三毒。因為真正見道的人不會陷落在道理上,一定會將自己洗心瀝腦的經驗與人分享,說不出自己如何改變,就是沒有修行的經驗,只好講籠統的道理。
則老碰到法眼文益,法眼文益是大成就的人,學問好、氣質高,學術界一致推崇他是禪宗的哲學家。這個推崇在禪宗看來一文不值,因禪宗與哲學家無法聯絡,學術界不瞭解,當然引喻失當。
法眼問則老:「什麼是佛?」則老說: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法眼再問:「什麼是丙丁童子?」則老答:「丙丁屬火,丙丁童子就是火童子。」法眼再問:「是先有火再有童子,還是先有童子再有火?」一路追究下去,則老冷汗直流。有個先後就是主客對立,有童子有火就有能所的分別,都不能圓滿地解決問題。窘了一段時間,法眼才說: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一剎那,則老的疑團煙消雲散,才知道真正的丙丁童子。
這裡留個空隙讓你思考,要把思考逼到牆壁,走投無路,才能破壁而出。這不是「言語道斷」嗎?斷了以後呢?「心行處滅」。這是同時存在,不能不提醒你。
見性之後,要知道尊重它、承當它、珍護它,如保護自己的眼睛。《聯燈會要.卷十一.汾陽善昭章》載有一段話:
汾陽善昭禪師,初謁首山,遇上堂。師出,問:「『馬祖陞堂,百丈捲席』,意旨如何?」山云:「龍袖拂開全體現。」師云:「師意如何?」山云:「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師於言下大悟,提起坐具,云:「萬古碧潭空界月,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便作禮。
百丈野鴨子公案,大家一定百聽不厭,馬祖道一扭擰了百丈的鼻子說:「又道飛過去了?」很不容易瞭解。一般人總以為這心放在野鴨子的身影上,被扭擰才知心跑掉了,這種常識話是道理上會意,和禪宗沒有關係。
關鍵在被馬祖扭擰鼻子時瞬間的痛覺,百丈捕捉到了什麼心靈震盪?時間非常短暫,百丈被罵,馬上回頭轉腦體悟到了,真的太聰明了!所以他回寮後一會兒哭,一會兒笑,體會得那種意識的曲折變化,怎麼不高興呢?他開悟了,悟得那個「心行處滅」的絕對意識。所以馬祖陞堂,百丈以捲席來表達謝意,因為陞堂講的法如何圓滿,都不如鼻子被擰「言語道斷」的實際感受。從此保任為上,不再聽囉唆的法了。
首山省念禪師才說:這是「龍袖拂開全體現」,堂堂正正地展露以法為生命素材的雄風,首山也自誇:「象王行處絕狐蹤」,什麼法要、三毒、八正道都是誆小兒的糖果,我首山是法王子,於法自在,自在逍遙啊!
聽完了首山省念的話後,汾陽善昭也發了一頓令人讚嘆的提示:「萬古碧潭空界月,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見性之初,有時能保持,有時會喪失,甚至沒幾天什麼也沒有了,空留一片美麗的虛幻回憶。這種特殊的心靈經驗,就如「萬古碧潭空界月」,人和月是相對的,必須透過正確的修行(再三撈摝)才能心法不二(始應知),展開以法為主的行履。
悟後起修,必然是相對意識與客觀的絕對意識磨合的過程,並不是要我們丟掉相對意識而採取絕對意識。相對意識是我們過活現實世界的必要工具,你仍然是工程師、清潔工,也許是達官貴人或是販夫走卒,都可以是令人尊敬的禪者,過的是調和相對意識與絕對意識的中道生活,也是善昭所講的「再三撈摝始應知」。用現代的語言講即超世與淑世並行,理想與現實平衡,既超越又寫實,以宇宙心輕鬆怡悅地在現象界過活,了無恚礙。